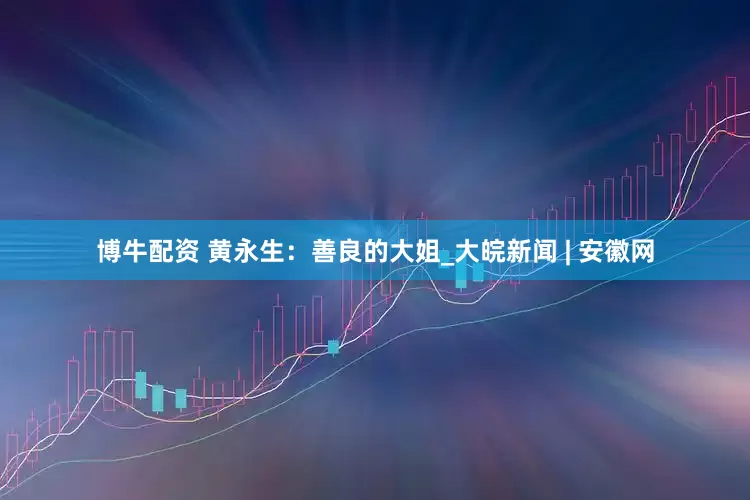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,一个午后,日光正烈,我骑着车匆匆往单位赶。行至省教育厅门前,眼见绿灯将熄,红灯将亮,我手下早压了车闸,车子缓缓向前溜着。不料前头一位大姐,大约也是见灯色将变,猝然捏紧车刹——我的前轮还是轻轻蹭上了她的后轮。未待回神博牛配资,只见她身子一矮,扶着车把,缓缓跌坐于地。
我的心猛地一沉,慌忙跳下车奔过去。只见她眉头紧锁,一手捂着脚踝。我连声道歉,小心扶她挪到路边石阶坐下。低头一看,脚踝处已浮起一片刺眼的红肿。“坏了!”我心头一紧,声音也发涩,“大姐,对不住!我这就送您去医院瞧瞧。”
说话间博牛配资,三三两两的路人已围拢过来。大姐忍着痛,摆摆手,声音还算平稳:“不碍事……我是妇幼保健院的,手头有份要紧的检验样品,得先送去安医大。”我连忙点头应下:“大姐,这样,我给您拦辆出租,您坐车走,自行车放后备厢,我骑车跟着,行吗?”恰巧,一辆黄绿相间的出租车在路边缓缓停下。受伤的大姐松了口气,果断道:“化验耽误不起,就按你说的办吧。”
我心头一热,赶紧搀扶她坐进车厢,小心把她的自行车塞进后备厢。向驾驶员预付了车费便关上车门,自己也立刻跨上车,奋力蹬行。那出租车很快汇入车流,消失在街角。我一路紧赶慢赶,心里七上八下:她的脚不知怎样了?到了安医大门口,会不会找不到人?
待我气喘吁吁赶到安医大门口,远远地,心却一下子落回了实处——那位大姐,竟一手扶着她的自行车博牛配资,单脚支撑着,静静立在梧桐树荫下等着我!午后的风吹起她额前几缕花白的头发。我鼻头一酸,冲上前去:“大姐,您怎么不坐着?”“怕你看不见我着急,”她笑了笑,额上还带着忍痛的细汗。我赶紧锁好自己的车,搀扶着她,一步一步,慢慢挪进了检验科大楼。
在等待结果的间隙,我瞥见她脚踝的红肿似乎又涨了一圈,鼓得发亮。“大姐,这不行!得赶紧去骨科看看!”我急得声音都高了。她却只是摇头,眉宇间只系着那份小小的化验单:“人老了,骨头不经碰,看着吓人罢了,不碍事的。单位等着这结果呢,耽误不得。”终于,结果出来了,她仔细收好,神色一松,反倒宽慰起我来:“别担心,我在妇幼院工作,看病方便。放心,这事儿我不会赖你。你帮我叫辆车,我自己回单位就行。”
听她言语恳切,一股温热的暖流蓦然冲上我心头:“大姐,您这样……还是让我送您回去吧?”她执意不肯,态度温和却坚决。那时节,手机还是稀罕物。我郑重地写下单位名称、个人姓名和办公室电话,塞进她手心,并给她看了看我的工作证,这才跑到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,小心扶她坐进去并把自行车放进了后备厢。望着那抹黄绿色渐渐融入城市的车河,我站在原地,久久没动。
此后许多天,每当办公室电话响起,我心头总会掠过一丝不安——毕竟惹了麻烦,总怕对方找上门来。然而,那听筒里传来的声音,从未与那个夏日的午后有关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这份悬着的心,也慢慢化作了深沉的庆幸与感念:我这是遇上好人了。
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,这件事也慢慢沉入了记忆深处。多年后的一次偶然机会,我恰好遇到一位妇幼保健院的医生。闲聊间,不知怎的又提起那个午后,提起那位脚踝肿得老高却坚持先送化验单的大姐,还有她那口依稀可辨的上海口音。那位医生听着,若有所思地点点头:“哦!你说的,像是化验科的李大姐,没错,上海人,院里公认的热心肠。”他顿了顿,回忆道:“是有这么回事。那会儿她女儿在上海快生了,她计划好要提前过去照顾。结果临行前,好像是脚踝扭伤了?在家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才动身。还好,紧赶慢赶,总算没耽误照顾月子,就是出发那几天,肯定急坏了。后来没两年,她就退休回上海了。”
我一时怔住,握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。原来,那轻轻一碰之后,她独自咽下的,远不止脚踝的剧痛和不便。为了那份化验单,为了不让我这个陌生人担责,她默默扛下了所有,甚至差点耽误了去照料待产女儿的计划——那一个礼拜的耽搁,该是怎样的焦心和煎熬?可那天,从始至终,她没对我皱一下眉头,没说过半句埋怨的话,只把那份宽厚和担当,稳稳地压在了自己的肩上。
谢谢您博牛配资,善良的大姐!
扬帆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